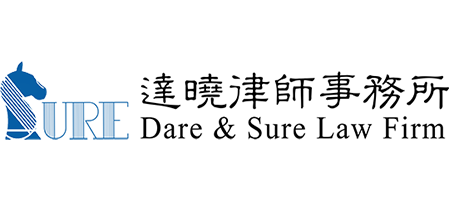张驰有道——评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实际适用
2019-08-01 10:03:50
单位:达晓律师事务所
邮箱:guoqiuyan@daresure.com
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为商标无效宣告的三种法定情形,一是违反商标绝对禁止注册理由取得注册的;二是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三是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而实践中,该条法律规定的适用程序、适用主体、适用对象曾引发过颇多争议;对如何理解“以其他不正当手段”一直是行政、司法实务界的难点;加之2019版商标法对本条规定增加了商标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的适用情形,进一步增强了商标使用对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
——引言
一、2019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立法本意早已有之
1
2019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颁布前的适用情形
2013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该条规定所在篇章为商标法第五章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根据该项规定本身的文义解释,其只能适用于己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程序,而不包括商标申请审查等未获得商标专用权的审查、异议、核准程序。而在实践中,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并无定论,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应遵循法律条文本意,支持该条款仅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商标无效宣告程序。该观点的主要依据表现为,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审查过程中,对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标注册的情形,审查主体更多的是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予以规制;而仅当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才会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我国商标申请注册量的逐年增加,商标争议案件受理量亦在大幅度上升。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就已发现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若待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撤销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还极大浪费了行政、司法资源,不利于维护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该条款既应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程序,还应适用于针对商标异议、不予注册等商标争议程序,应当贯穿适用于商标审查、核准、异议、争议全部阶段。
在2019版商标法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实际审判中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认为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核心主旨及立法精神在于贯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如仅根据该项规定的文义解释,其只能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则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只能在商标注册后方可适用该条款来约束不正当注册行为,这种事后救济反而不合理占用、浪费了行政、司法资源,甚至会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因此,维护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撤销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评委(现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人民法院在商标审查、核准行政程序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可以参照前述规定,制止不正当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
2
2019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修订目的
随着商标恶意申请注册行为和争议案件的不断增多,从源头上制止恶意申请注册行为已经成为立法者、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使商标申请注册回归以使用为目的的制度本源,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维护好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成为2019版商标法的修订主旨。2019版商标法于今年4月23日颁布后果然不负众望,在条款设置上对恶意注册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制。以2019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修改为例,该条修订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在商标绝对禁止注册理由处增加了“商标局可对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予以驳回的权利”,以及“限制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册商标的类别和范围”。
这一规定的修改,真正做到了将规制恶意注册行为贯穿于商标审查、评审程序的始终,做到了有法可依,不再是依据立法精神参照适用,而是支持所有人(商标局可依职权/任何人可依申请)对恶意注册、囤积商标的行为均可提出无效宣告申请。这样一来,商标实际使用人在应对他人(尤其是恶意抢注人)已经注册商标的方法不再仅仅限于放弃已使用商标,或是花费巨资向恶意注册人购买注册商标,而是可以通过申请宣告已注册商标无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由此有效的避免了已使用但未注册商标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是打击恶意注册、囤积商标行为的有力举措。
二、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类型
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表述,仅概括性指出违反商标绝对禁止注册理由,及采用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况。其中,违反商标绝对禁止注册理由有相应的法条列举,如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情形,2019版商标法还增加了第四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的情形;但仍未对采用欺骗手段和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细化规定。尤其是“其他不正当手段”这种兜底式措辞,使具体情形更加扑朔迷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17年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二十四条对“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了解释,即“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同时,《商标审理标准》中亦对此进行了细化,即:(1)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2)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字号、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名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3)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大量商标,且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三、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情形及分析
严格来讲,立法机关、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由于其职能的区别,在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方面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立法机关关注的是法条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一般会更注重从字义本身对法条进行解释,反对扩张性、迁移性的适用,否则将不利于社会公众对法律判断的预期及对法律权威的尊重。行政主管机关则更为关注行政管理内部的统一协调,避免出现审查或执法标准的差异性;同时,行政主管机关面对海量的商标申请及争议审查程序,管理效率也必然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行政主管机关在法条解释方面也会注重其效率性。司法机关则更为关注个案,在具体案件中能否体现个案公平是其解释法条的最主要目的,因此司法机关在个案审判中最有动力和意愿对法条进行扩张解释。
虽然存在上述差异,但立法机关、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面对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实际适用时,遇到的情况其实大致相同。本文尝试总结如下:
1
对商标相似程度的认定
原则上讲,商标获准注册前必须经过与在先商标进行比对并审查其显著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主管机关有必要检索和评判申请商标与在先商标对比情况下的近似程度,若近似度过高,则申请商标不具备显著性而应驳回其申请。可以说,商标的近似度已经可以对申请商标进行一票否决。
但同时,商标近似度也是行政主管机关及司法机关在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一个考量因素,如果申请主体所注册的商标均为抄袭他人商标的情形,将很有可能被认为采取了“其他不正当手段”。如在(2018)京73行初4577号判决中,法院考虑到第三人连续申请注册了包括本案诉争商标在内的4件商标,且该4件商标图样与引证商标图样几乎完全相同。在案证据显示,第三人与原告门店的营业地点相邻。且第三人经合法传唤而拒绝到庭陈述意见或说明理由,上述情形的出现显然难谓巧合。鉴于此,法院认为第三人之前述商标注册行为明显具有侵犯他人在先权益、扰乱商标正常注册秩序的故意。又如(2018)京行终4434号判决中认定,嘉万达公司先后注册“林书豪”、“趣多多”、“炫迈”、“iPad”、“miumiu”、“凌仕”等24件商标,其大量摹仿知名商标,注册数置已超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并无法对其大量注册商标的意图及相关商标的设计创作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上述行为已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并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商标近似程度既可能构成阻却商标申请的认定要件,还可能先作为依据认定申请主体存在使用不正当手段的行为,进而阻却商标权的授予或存续。那么,在现实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中,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两种路径如何进行取舍,将成为一个难题。在已经可以以存在近似商标而缺乏显著性作为阻却理由的前提下,还需不需要讨论其作为“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要件?或者单独以相似程度评判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能不能与其他要素相结合来判断申请者是否存在恶意,再进而认定其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商标,最终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进行规制?这其中的取舍和尺度的把握,将是商标授权行政程序及司法程序中的一个挑战。
2
对“囤积”商标行为的认定
通常认为,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主要规制的是扰乱商标注册程序并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过程中,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申请主体是否不以使用为目的地大量囤积商标。
个案中,对“大量”的规模判断及“囤积”的性质判断是相对模糊且困难的。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单纯从一个数字出发来认定“大量”和“囤积”情形的存在与否,往往还需要结合其他涉案因素来综合评判。如是否具有抄袭、复制他人高知名度商标的故意、是否存在同业经营、是否存在商业使用可能等情形,都在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考虑范围内。如(2016)京行终475号判决中,法院认定刘红群在29类、30类、32类上申请注册了‘facebook’商标,还在第29类商品上注册过“黑人”、“壹加壹”等商标,其上述注册行为具有明显的复制、抄袭他人高知名度商标的故意,这种以囤积商标进而通过转让等方式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显然违背了商标的内在价值,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甚至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故该种旨在大量抢注、扰乱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但案件中被抄袭的商标标识数量并不算多,法院认为大量抢注的结论亦结合了复制、抄袭他人高知名度商标,及针对同一枚商标在多个类别申请的情形。
又如(2017)京行终601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仅证明姜惠娟除本案被异议商标外,还在5个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SECRET”商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均属于与被异议商标的第30类咖啡等相关的服务或者日常生活用品及服务。对于姜惠娟而言,均具有使用的可能性,尚不足以证明其具有囤积商标的意图。本案涉及的商标数量同样不多,但却因存在商业使用的可能而未被认定为囤积。
3
对善意受让商标主体的保护
商标的初始申请主体实施了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禁止的“其他不正当手段”并获得了商标授权,目前的通常做法是,这类商标应该予以驳回、撤销。现实中还存在一种情形,在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申请主体所谓“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规制之前,涉案商标已经进行了转让且受让者对初始获取该商标的“其他不正当手段”情节不知情,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如何处理,也是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事实上,多个商标由不同主体分别拥有、而各主体之间存在资本或企业组织架构上的控制或关联关系的情形并不少见。这种安排有时候是为了经营活动需要,有时候是为了降低商业风险,但也不排除存在控制或关联关系的主体借此分散商标权利,以规避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囤积商标等“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因此,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判断是否存在商标囤积行为的时候,还需考虑存在控制或关联关系主体的持有商标的总量。申请手段的不正当、申请行为的恶意不应当被这种“协同分工”的游击战所掩盖,若存在控制或关联关系主体的持有商标总量较大,又不存在商标性使用的情形,那么这些主体应当被认定为囤积商标无疑。如在(2015)京知行初字第2997号判决中,法院认为诉争商标“捷豹”的原权利人在商标评审案件中与代理机构签订商标代理委托书中的联系人与受让人公司股东姓名相同。且除诉争商标外,诉争商标原所有人还申请注册了“百度”、“SOhO”、“路虎”、“陆虎”、“Jeep”、“吉一普”、“SOROS索罗斯”、“MICHAELJACKSON迈克杰克逊及图”、“FBI”、“史泰龙STALLONE”等多个与他人在先权利标识相同的商标。可以认定,诉争商标原权利人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抄袭、摹仿他人商标的故意,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亦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并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故诉争商标原权利人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为亦有明显逃避法律追究的嫌疑。
而另一种情况则需区别对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非法申请获得的商标经合法转让后,商标权归于善意第三方,此时如果一味强调获得手段的不正当性而一刀切地对该商标认定无效,即使善意第三方可以从转让方获得转让对价的赔偿,仍会因为持有商标的被无效而极大地影响其经营活动,甚至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如(2018)京行终6281号判决中认定虽然诉争商标的原申请人申请注册了106件商标,不排除其具有商标囤积行为,但是本案诉争商标已经转让给奥商公司,且拉多芮公司未能证明徽商公司与奥商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在诉争商标不违反商标法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对于合法受让诉争商标的奥商公司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适用该项规定时,应当结合个案的情况进行判断,拉多芮公司关于其他无效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徽商公司不正当行为不是本案诉争商标应被宣告无效的当然理由。
综上分析和举例,笔者对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持合理扩张解释的态度,但这种扩张解释也不是无边界的、不受约束的。实践中,个案需要考虑的要点千差万别,审查主体和审判主体又各自有其主观倾向和价值判断,很难形成一套普适的、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标准。因此,如何在保证个案审判效率和灵活的同时,又维护商标法的刚性和权威,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结语
大量在先判例和2019版商标法对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修改均说明,适当对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进行扩张解释,符合立法主旨且能有效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应当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由于个案的差异性较大,在追求个案公平的过程中,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需要考虑的因素很难形成统一标准,因此难免出现尺度不一的情形。如何在法律的刚柔之间、权威和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将是商标法立法、执法、司法主体之间还需长期讨论和博弈的话题。
【参考文献】
郭建广《试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适用问题》,2016年07期《中华商标》
熊北辰《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规制》,2019年02期《中华商标》
邹岭《解读2019年版<商标法>》,2019年7月9日知产未名微信公众号
杜颖《理解<商标法>第44条第1款的两个立场和三种方法》,2017年8月25日《IP影响力》
李笑冬《<商标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的解读》,2018年11月30日《IPRdaily》
燕思宇《关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适用》,2019年6月28日燕思宇微信公众号
(2015)京知行初字第299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6)京行终475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京行终601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8)京73行初457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8)京行终4434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8)京行终6281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