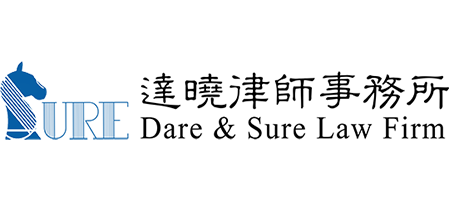虚假广告还是虚假宣传,“直播销售”行为法律适用的另一种思考
2020-10-22 13:40:44
单位:达晓律师事务所
邮箱:zhusirui@daresure.com
现行实践中,无论是立法语言还是司法裁判,均对商业宣传和商业广告缺乏明确区分标准。《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未阐明宣传行为和广告行为的实质内涵,均仅从相关行为的外延进行界定,且两者外延重叠很大,缺乏区分。虽然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构成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属于广告的,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处罚。似乎已将虚假广告与虚假宣传划分为特殊与普通的关系,厘清了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发生法条竞合时的适用顺序,但并未解决宣传和广告行为如何区分判断的问题。
在各种新媒体及新型传播方式层出不穷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集合多种行为内容为一体的各类文化公司、经纪公司、传播公司。这也导致《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原有那种通过外延界定行为的立法语言日益无法适应新型广告和宣传的现实监管需要。而如果说法律语言是对社会交互行为进行归类和命名,那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广告与宣传概念的混淆又并非仅仅是法律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广告和宣传行为客观上有无区分的问题。
一、广告与宣传的区分标准——结论或许是无法区分
1
载体无法作为区分标准
直白地说,从文义理解,《广告法》实际未限定广告载体(《广告法》第2条中所表述的“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实际是缺乏法律效果的表述,甚至可以视同语气助词)。
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涉及虚假宣传的条款分别位于第5条第4项和第9条两处,整体来说,共包括3种情形:“在商品上”“利用广告”“利用其他方式”。2017年及201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再规定虚假宣传的情形,但可以理解为仍然包括“在商品上”“通过广告”和“通过其他方式”这三种。[1]《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宣传载体的范围似乎比《广告法》第2条的表述要明确一些,虽然仍存在“通过其他方式”这种解释空间极大的兜底条款,但至少“在商品上”“通过广告”明示了标签也属于宣传载体,同时暗含宣传与广告之间的普通与特殊关系。
当然,广告也同样可以在商品上进行呈现,虽然商品包装上的内容并非都构成广告,但除了法律、国家标准要求必须标注的事项外,其他内容若符合广告特征的,也可以适用《广告法》监管。[2]
因此,就载体来看,无法将其作为广告和宣传的区分标准。
2
以传播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公众作为有限的区分标准
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观点,即以传播对象是否针对不特定公众来判断是否属于广告行为。“广告”二字的语义观感即是“广而告之”,暗含针对不特定多数的意义。在一些行政案件中,亦认定广告法保护的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公共利益,[3]由此逆推,广告的传播对象一般为不特定公众。
但此种区分方式的局限在于:一方面,无法将对不特定多数的宣传行为和广告行为作区分;另外一方面,对于不特定公众的界定,在新型媒体层出不穷的今日,缺乏统一标准。譬如微信朋友圈内的宣传行为,以及直播销售方式,往往需要受众先进入宣传主体所在平台的对应网络空间,微信需要添加好友,直播需要注册后进入特定房间。因而能否将对特定网络空间内的用户进行宣传的行为认定为对不特定公众进行宣传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判断。如果进入和阅览该网络空间(微信朋友圈、直播房间)的途径具有开放性,则默认为不特定公众均有进入和阅览的可能性。即便进入该空间需要一定条件,比如注册用户、缴纳费用、身份认证,但条件本身可期待不特定公众均能完成,则该网络空间内的宣传行为仍具有公众性。从这个角度,一般来说,直播营销必然具备这种公众性,而微信朋友圈则因人而异。
3
宣传内容是否针对商品和服务不再作为区分标准
从《广告法》的定义来看,广告应当是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服务,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限定为是对商品的各类要素进行虚假宣传。但是,从司法审判的案例来看,并未因此将公司对其自身的宣传排除在虚假广告或虚假宣传的范围之外。从下文列举的司法判例来看,虽然一些判决支持了监管部门将企业自身宣传行为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而非《广告法》进行规制,但总体而言并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观点。回归《广告法》自身的定义,广告本身包括直接介绍和间接介绍,所以自然也包括对企业的推介宣传乃至企业境况的客观介绍,上述企业介绍虽然不必然直接指向具体产品和服务,但其最终效果仍然指向经营行为,进而延伸至其产品和服务,其目的仍是使消费者认可企业,从而购买商品或者服务。[4]当然,如果宣传主体系自然人个人,行为本身也不具有经营属性,则虽是业务内容的介绍,也仅能认定为个人的生活行为,同时不具备商业宣传和商业广告的属性。[5]从这个角度看,单纯以宣传内容为标准,无法区分广告行为和宣传行为。综上所述,从行政处罚的实践来看,现行执法习惯也愈发将企业自身的宣传纳入广告的监管框架下。
二、看不见的裁判观点
在已有的司法审判中,大部分法院的裁判观点并未对广告与宣传如何区分进行明确说理。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相对人都会以其行为不是广告而是宣传(或者反之)进行抗辩,因此法院往往并不将违法行为属于广告还是宣传作为争议焦点进行认定和阐述。另一方面,可以作推测,现行司法实践中其实亦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
例如,在某电信技术公司诉某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判决[6]中,法院认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认定条件进行了规定。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作为专有名词具有特定的含义。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扶持,而且可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美誉度,暗示企业具有较高成长性、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而涉案公司未经相关部门认定,在网页中宣传公司自身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该公司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由此,其宣传行为构成了虚假商业宣传。涉案公司虽然在其宣传用语中未直接对其商品进行表述,但通过宣称其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对企业形象进行宣传的目的,足以使消费者对其生产经营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产生误解,从而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综合以上情况,法院认定涉案公司实施了虚假商业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而在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威科亚太公司)诉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判决书[7]中,威科亚太公司主张其在微信公众号中功能介绍的表述不属于《广告法》规范的广告行为,而属于宣传行为。针对上述意见,法院以《广告法》第2条的规定出发,认为微信公众号是一种企业推广的有力途径,威科亚太公司在其公众号功能介绍中表述“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Kluwer)旗下全球财税第一品牌CCH”,从所属集团、专业领域、服务品质等方面介绍威科亚太公司的服务,认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商业广告行为。
比较上述两份判决,企业均是通过网络面向不特定公众对企业自身要素进行的介绍,但前者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虚假宣传,后者认定为《广告法》规制的虚假广告。笔者检索了同时涉及《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判决——很多案件之所以涉及两部法律,仅仅是因为被诉机关以涉案行为违反《广告法》进行立案,而最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处罚——少有对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进行区分的明确说理。
三、新旧法衔接——从“我是虚假广告”到“我是虚假宣传”
在对《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其实会涉及至少四部法律文本的比较: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及201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2015及2018年的《广告法》。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明文确立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的法条竞合关系,但这一点似乎并未对影响基层执法实践产生可见的影响。法律演进对基层执法的影响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对应罚则的变化上。
在对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的行政监管中,但凡涉及处罚案件,当事人常会以法律适用不正确为由进行申辩。吊诡的是,在笔者所见不同时期的案例中,在2018年以前,当事人经常主张其行为系宣传行为而非广告,而在2018年以后,则出现以其行为系广告而非宣传行为进行抗辩的情形。
最初,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虚假宣传对应的罚则是一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的罚款;1995年2月生效的《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罚款数额为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而后,2015年9月修订生效的《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的罚款数额提升为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广告费无法计算或者过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此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变化。现如今,2018年1月生效的以及2019年再次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与《广告法》看齐,将虚假宣传的罚款数额提升至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在此一番法律更替的背景下,在2018年,当事人如果没有相关广告经营者同其佐证广告费用,则《广告法》的处罚数额必然远高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到了2018年后,因《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罚款数额同《广告法》保持基本一致,当事人则更愿意寻求某位“广告经营者”,做低合同呈现的广告费,从而避免高额处罚。虽然在此情形下,广告经营者也同样面临明知虚假广告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违法责任,但是,如果广告经营者位于异地,则必然经历案件移送、当地部门重新立案等各项程序,待到处罚广告经营者时往往人去楼空。另外,如果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按广告费计算的罚款数额仍低于二十万,对于当事人来说,则仍可通过代缴罚款来实现降低处罚的目的。
可以看出,现行有效的《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的罚款数额基本相同,因此认定虚假广告还是虚假宣传,区分的现实意义似乎仅存在于案件涉及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的情形下。当然,从逻辑上看,广告行为是在先的概念,有无广告费,是否存在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似乎不应影响广告和宣传行为的区分认定。但是,从法律实践出发,如无法确定各方主体,那对广告行为的规制又变成缺乏对应主体的空洞概念。
四、直播带货与商业广告——没有不同,但可以不同
沿着前文第一部分的逻辑,在宣传行为和广告行为缺乏严格分界的背景下,以我们理论上认定商业广告所考虑的基本要素,直播带货行为理应纳入商业广告的范畴进行规制。但在直播带货行为中,直播平台、作为自然人的主播和主播背后的经纪公司,无法完全对应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这就将导致前文第三部分提到的困境:将广告概念套用于直播带货行为后,如不改变原有制度框架下对广告各方主体的定义,则难以确定直播带货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
比如,一方面,单纯从外观看,直播营销行为和传统的电视购物广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虽然电视广告可能有内容备案和事先彩排预演,而直播带货行为具有高度的临时性和不可控性,但是否是临时演绎并非判断是否属于广告的考虑要素。从这一角度,直播平台似乎和传统的电视台一样,在直播带货中是作为广告发布者而存在的。而另一方面,从直播带货的实际效果来看,直播平台往往并不为商品信息的发布提供资源、流量的外部支持,相关资源、流量系由主播带动。直播平台不介入具体宣传行为,而是作为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其中。[8]同时,传统电视台作为发布者,必然存在广告发布的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亦会收取明确的广告费,而直播平台作为公众开放平台,其直播信息系用户任意发布,平台不必然参与营销分红。类比微信平台,即便我们将一些公众号的内容视为广告,一般也不会将微信平台视为广告发布者。
另外,亦是从外观上,直播的网红本人和传统电视广告中的出演明星类似,都会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但是,现行的网络直播的商业模式并不同于传统的“电视广告+门店营销”的形式。现行直播的商业模式众多,其中存在“直播+虚拟礼物”“直播+电子商务”“直播+服务”和“直播+广告”等多种模式。而在“直播+电子商务”模式下,直播网红往往直接发挥广告设计者乃至产品经营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自然人的直播网红和其背后的MCN机构在广告行为中如何划分主体地位和法律责任,亦是广告监管中无法绕开的问题。虽然《广告法》并未将代言人限定于自然人,但MCN机构并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商品推介,实践中,其有时兼具网红经纪人和广告设计者甚至广告经营者的身份。
从更深层的角度总结,《广告法》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各方主体责任,一方面是对这些从事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行为的主体进行法律上的命名,是将事实予以法律规范化。[9]另一方面,对各方主体的认定,亦是赋予其具有公法上的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从现行行政监管的逻辑来说,需要认定这些主体应当做到宣传内容合规性的审查义务,进而才能在虚假广告发生时,由客观的违法情形推定这些主体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这是将法律责任进行事实还原。而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事物的出现,虽然从“将事实进行规范化命名”的角度,很容易将直播带货定义为广告,将直播平台、作为自然人的主播和主播背后的经纪公司一一安排进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的位置内,但本质上是对新型的市场主体赋予此前并未要求的公法上的注意义务和责任。这种赋责的行为,不宜过于“当然而然”。而在直播带货各方当事人难以认定是否属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的情况下,鉴于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本身处罚力度极为相似,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对直播带货进行规制,也算是一种过罚相当的不错选择。
上一篇:浅析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
下一篇:直播带货将迎来“强监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