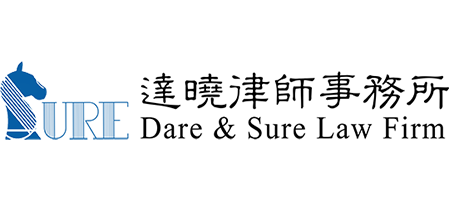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
2019-12-26 09:59:02
单位:达晓律师事务所
邮箱:xiezhijie@daresure.com
2019年12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全文共29条,其中第二十六条是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认定的规定:“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合同)之性质,在上述司法解释公布之前,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一直未有十分明确的定性。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中经常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其仲裁条款的效力就成为基本争点之一。
本文从一起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切入,围绕该案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尝试逐步展开探讨涉及的以下问题:一是合同性质如何认定,该份协议是否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二是合同属性如何界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协议?三是可仲裁性如何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是否可仲裁?四是仲裁条款效力如何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五是溯及力问题,新《行政诉讼法》规定是否适用于该法实施之前订立的合同?六是仲裁条款适用的分割,区分协议中的可仲裁内容与不可仲裁内容。
一、基本案情:一起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
A县政府和B物流园公司(协议中的“甲方”)与C投资公司(协议的“乙方”)于2009年5月签订了《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产品物流配送综合市场项目投资协议》(简称《投资协议》)及《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产品物流配送综合市场项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在A县的B物流园内投资建设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产品物流配送综合市场,甲方承诺以出让或其他任何合法形式提供园区建设项目用地,并给予相应配合协助和各项税收及规费奖励与优惠。同时,明确约定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D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为终审裁决。”
乙方认为自己积极履约,但甲方却未按《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由于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2019年4月,C投资公司依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向D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5月,D仲裁委员会受理。2019年7月,A县政府和B物流园公司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申请并立案[1]。关于《投资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之有效性问题,成为该案的争议焦点。
二、合同定性:以合同主体内容认定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
合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主订立的,而合同文本多是由当事人自行拟定的。我们对任何法律概念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极可能出现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完全对应的情形,而合同性质的认定与合同主体、管辖权以及法律适用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换言之,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2]
本案《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明确界定了交易结构、交易目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而约定的核心内容是C投资公司在A县C物流园投资建设综合农贸市场,A县政府承诺以出让等形式为其提供园区建设项目用地,并具体约定了地块位置、面积等。根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属于包含多个交易行为的复合交易,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财产转让以及C投资公司负责投资、施工和运营的内容。
根据合同的主体内容认定,本案《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
三、合同属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属性的争议性
1
行政协议说
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此条正式将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问题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并未在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中明确予以规定,使得其是否属于“其他行政协议”的范畴成为了被广泛争议的焦点。
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典型案例莫过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6号“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3],法院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 照理来讲,法院要将该案作为一起行政案件来审理,首先应当对土地出让合同的性质进行阐述和判断,但是一审、二审判决书上并没有相关分析和认定[4]。该案主审法官的解释是,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律职责,其诉求具有很明显的行政法性质,单个地看,都可视为一个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也没有提及合同纠纷,所以,法院就“直接作为行政案件”,由行政庭审理,对出让合同的法律属性也不加考证。[5]
2
民事合同说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以土地使用权出让为主体内容的协议,在实践中普遍被认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作为民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和《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11〕41号)将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归类为民事案件。
其次,在审判实践中,司法裁判也普遍将之作为民事合同纠纷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时间集团公司与浙江省玉环县国土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6],崂山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7],玲嫚与黑山县国土资源局、黑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8]。据学者统计,截止2019年5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4766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民事案由4700件,行政案由66件,而行政裁判仅1例产生于2014年之前,年限分布具体如表1所示。[9]
最后,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创设的是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出让合同。”则土地出让方的权利主要是向受让方收取土地出让金,义务则是按照合同约定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受让方的主要权利是受让土地使用权,按照合同使用土地,包括出租、转让、抵押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经济活动,主要义务则是缴纳土地出让金。
四、可仲裁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仲裁符合《仲裁法》
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争议是否可适用仲裁规则,一方面需正向理解,是否符合《仲裁法》第二条关于仲裁受案范围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反面解读,是否存在《仲裁法》第三条关于排除仲裁的事项。
首先,《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如前所述,本案《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认定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其主体内容属于对财产转让、投资经营开发等方面的约定,相关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合同的仲裁管辖权由《仲裁法》明确赋予,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尊重。
其次,《仲裁法》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其中,可能需要讨论的是“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了行政复议范围,即除所规定的可复议事项之外的其他行政争议不可复议。换言之,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内的行政争议事项。[10]
最后,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的可仲裁性也得到我国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的确认。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GF-2008-2601)第40条载明,这类协议可以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一些司法裁判直接认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例如,大连市中级法院在大连春滨木业有限公司与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11]中认定:“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签订的,无论案涉合同系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因履行该份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均不属于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申请人主张案涉仲裁条款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五、仲裁条款有效: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仲裁条款有效性要求
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需要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一般要求。《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本案《投资协议》“第九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明确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D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为终审裁决。”该条明确表达了双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了争议事项即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选定了D仲裁委员会。而且,不存在《仲裁法》第十七条[12]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
因此,本案《投资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六、无溯及力: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继续承认土地使用权出让争议仲裁条款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在存在新旧法律衔接问题的情况下,一般适用“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合同性质的判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属实体问题。本案《投资协议》成立于2009年,不管之后法律如何修改,都不应影响原有协议仲裁条款的效力。
上述观点也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司法裁判中。例如,在张关六等与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人民政府土地协议案[13]中认定:“对于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在李昭君与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政府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案[14]中更是明确指出:“本案所涉及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是《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修改后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此之前,一直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没有溯及力。”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即行政协议司法解释没有赋予其溯及既往、排除仲裁管辖权的效力。
七、意思自治: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和依法裁判应当得到尊重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得到最大尊重。A县政府、B物流园公司与C投资公司于2009年5月签订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签署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当予以遵照执行。《投资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只要没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条款无效情形,也都应当予以遵照执行。因此,对于申请人所提的协议履行的违约和损害赔偿的问题如何判断,属于仲裁机关的审理范围。
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和依法裁判应当得到尊重。虽然本案《投资协议》有部分内容涉及税收优惠等行政措施,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仲裁机构对相关民事争议的管辖权。如果仲裁机构越权审理,人民法院还可以依法行使司法监督权。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与仲裁裁决的合法性审查,应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两个面向问题。[15]如若因为存在超出民事关系的可能性而剥夺原本因为民事关系而产生的仲裁管辖权,属于人民法院的越权。
在仲裁管辖出现歧义时,通过合理解释以尽可能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维护诚信履约,也是我国通行的司法实践。例如,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明发集团无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国土资源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16]中认定:“本案中,《无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为民事合同,仅有部分内容涉及行政措施,故从维持合同条款有效的角度出发,在理解涉案仲裁条款中‘一切争议’的含义时,应对其进行限缩性解释,将与民事纠纷无关的争议排除在‘一切争议’之外。故合同中关于仲裁的约定,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的范围。”
综上所述,本案《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违约赔偿等争议事项的仲裁条款,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1] 案件进展可关注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4民特20号投资协议仲裁条款效力纠纷案。
[2] 参见中国法院网:“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湖南平江县法院判决童某诉徐某、秦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载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4/id/2741945.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8日。
[3] 参见中国法院网:“指导案例76号 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载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1/id/2502922.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8日。
[4] 参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4)安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萍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
[5] 参见余凌云:“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亚鹏公司案’为分析样本的展开”,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5期(总第103期)。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3期(总第125期)。
[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陈鑫范、吴明熠:《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混合属性解析及其司法救济适用:基于双阶理论的思考与修正》,载《法学》2019年第4期。
[10] 参见王世涛、刘俊男:“行政协议争议解决之仲裁问题研究”,载《南海法学》2019年第3期。
[11] 参见大连市中级法院(2016)辽02民特78号民事裁定书。
[12] 《仲裁法》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
(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785号行政裁定书。
[1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675号行政裁定书。
[15] 参见姜波、叶树理:“行政协议争议仲裁问题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6] 参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特209号民事裁定书。
上一篇:如何才能当好“吹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