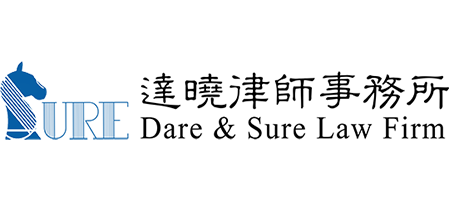“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一点冷思考
2019-12-12 14:33:23
作者:薛政
单位:达晓律师事务所
邮箱:xuezheng@daresure.com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该规定被舆论普遍评价为行政诉讼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在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一书中也认为,“允许由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立法机关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规定了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1]
近年来,最高法院和一些地方法院都对外发布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典型案例,并将此类案件称之为“新类型案件”,看作是新行政诉讼法的制度成果,认为正是新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请求权,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就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的判断权。”
从宣传或者宣示意义上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回归到规定本身和司法实践,我们应该明白,这类案件并不那么“新”,也不应算在新行政诉讼法制度成果的账上,人民法院就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的判断权更不是从此而来。
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这里的“依据”,就是应当适用,人民法院没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参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下发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的观点,应理解为人民法院“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至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纪要》认为,因为“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应当说,《纪要》的上述观点是符合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精神的,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一直是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判断和适用的。
以任建国不服劳动教养复查决定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3期)为例,针对被诉劳动教养复查决定所直接依据的省级政府规章《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企业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规定》,山西省离石县人民法院认为,“能作为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依据的行政法规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三个法规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审批和管理办法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但都没有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另定执行措施的规定。这三个法规中规定的适用劳动教养的对象很明确,根本没有《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企业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规定》第八条第(二)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该案二审的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更是明确提出:“可以参照的规章,是指那些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对于那些不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或者其内容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章,则不在人民法院参照之列。”我们看到,该案的两审法院事实上直接对省级政府规章有关条款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值得一提的是,该案一审判决的作出时间是1992年12月5日,仅比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的时间晚了两年。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现行法律上白纸黑字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即便有,规章也不属于审查范畴——该案两审法院对省级政府规章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胆量”正是来自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更准确地说,是对规定中“参照”二字所必然内含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权力的取用。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5号——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法院明确了“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的态度。
这两个案例都早于行政诉讼法修订,但即便在当时,也算不上“异类”。从逻辑上说,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性由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共同支撑,因此,法院对行政行为事实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和对法律依据合法性的审查是行政审判不可或缺的两翼,也是完整的行政审判权力的内在要求。它当然不可能在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近30年的时候,才由一个修订条款去赋予。
也有观点认为,新行政诉讼法通过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请求权”,进而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成为了法院的“法定义务”。这个观点似是而非。难道当事人不请求,法院就可以不审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吗?就像有学者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进行实效性考察后认为,最高法院公报案例涉及的20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法院对其中14个文件(占比约70%)未经审查就将其作为裁判依据予以适用。另外,通过对上海地区法院相关案例研究后认为,在30个行政诉讼案件中涉及的54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法院对其中9个文件明确作出了合法性审查(占比约17%),其余45个文件(占比约83%)则属于“未经审查、直接适用”或者是“回避审查、不作评判”的情形。[2]
这怎么可能?
行政诉讼中,法官对行政行为,尤其是侵益性行政行为的审查,对行为所依据的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限、与上位法是否抵触、与同位阶规范是否冲突等问题是当然要进行审查和判断的。这是“规定动作”,如果不做,就可能办错案。对这个问题做实证研究,不能仅从法律文书上是否记载了审查过程来看,如果最终得出七八成以上的行政案件法官对规范性文件“未经审查”或“回避审查”的结论,也是不符合审判实际的。
所以,我们或许不需要过分拔高新行政诉讼法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制度意义,也不需要为了体现新行政诉讼法的制度成果,费尽心思在狭窄的时间窗口去挑选甚至“打造”一批这样的案例。如前所引,我们一直不缺乏这样的经典案例,在过去的30年,而不是4年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39页。
[2] 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页至第61页。